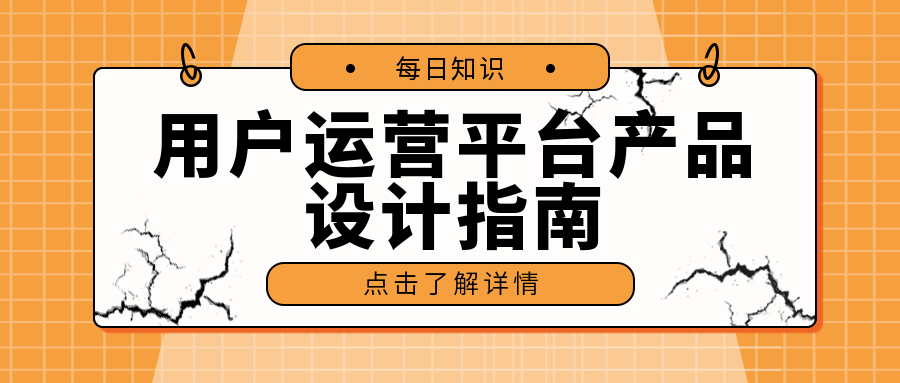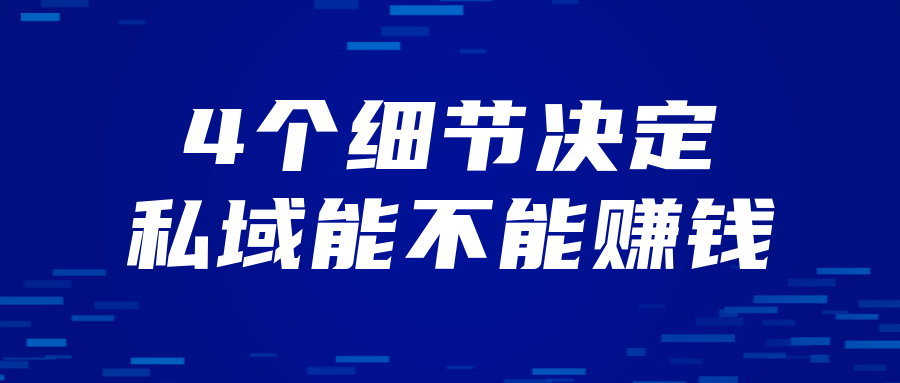为什么时间管理让我们越来越累?
时间管理是帮助我们把握时间长度的技巧,却没有提示我们使用时间的“深度”
时间是现代社会运转的经纬线。时间规范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对多数人来说,什么时候睡觉并不取决于是否有睡意,而是取决于时钟是否显示了可以入睡的时间,什么时候吃饭并不取决于腹中是否有饥饿感,而是取决于“饭点”是否到了。
这样的状况可不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之初便有,据科技史家刘易斯 · 芒福德在巨著《技术与文明》中所述,机械时钟的最早使用始于13世纪欧洲的寺院,用于帮助人们准时地参加宗教活动。而直到公元1345年左右,欧洲人才开始普遍接受将一小时分为60分钟,把一分钟分成60秒。也是自从那时起,时间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种“抽象框架”,越来越成为“人们行动和思考的参考点”。之后的几个世纪,时钟走出宗教领域,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芒福德甚至认为,工业革命中最关键的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到了现代社会,时间本身甚至就成了一种“宗教”,“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
于是“时间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无疑就成了现代人所必须掌握的一种工具。显然,时间管理对于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业绩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客观效果的提升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并不一致。很多人可能有这种感觉,即便已经对每月、每周、每天的时间做了很好的规划,执行得也不错,但是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深感事情永远都做不完,甚至感到心力交瘁。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理论上能提升时间利用效率的时间管理会让我们越来越累呢?另外,社会学家早就发现了一个与之相关联的“时间悖论”: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总体上一直呈增加的趋势,但人们主观上却觉得自己的闲暇时间在减少,也就是说,人们实际拥有的时间越多,主观感受拥有的时间却越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时间管理有其固有缺陷,它只能解决我们与时间相处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在更广泛的情景中,时间管理是无能为力,必须另觅他法。首先,人们总是无法准确地做出时间规划。人工智能科学家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在其名著《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侯世达定律,即实际做事花费的时间总是比预期的要长,即使预期中考虑了侯世达定律。
首先是因为事情的复杂度往往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因此也正如帕金森第一定律所言:工作会自动膨胀,直至占满所有可用的时间。
其次,人们无法预估未来发生的意外事件,而意外事件总是频频发生,打乱人们的原定计划。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鲍曼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流动的,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变动不居的,一切都处于不确定性中。
再次,从时间取向(time perspective)这一心理学概念来看,时间管理是一种未来取向的做法,而一味强调时间管理,就会使人们处于未来取向的单极状态,而这种单极状态会使人们的生活失衡。
心理学家认为,理想和健康的时间观念应该是过去取向、现在取向和未来取向的平衡,人们可以应生活情景的不同而适时转换与之相称的取向。比如在工作场景中采用未来取向,而下班回到家里,应该立即把工作内容抛诸脑后,采用享乐主义的现在型取向,尽情享受当下的闲适和放松。但是,现代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工作和生活混淆起来,在生活和闲暇时也不忘工作,休息时也要想着明天要干什么、还有哪些事没做完,那么自然就会觉得非常疲惫。
最后,时间管理是帮助我们把握时间长度的技巧,却没有提示我们使用时间的“深度”。例如,同样是安排闲暇的时间,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的“被动式休闲”所带给人的满足感,就远远不如从事一项自己的业务爱好所带来的满足感。在看电视时,我们可以一边嗑瓜子、玩手机、跟人聊天,我们并没有倾情投入,而在从事某项爱好时,我们就可以完全沉浸其中,甚至进入“心流”状态,因此我们从闲暇中获得放松和满足的程度并不取决于闲暇时间的长度而是取决于其质量。
出于以上四点,我给出如下建议,来改善我们与时间的关系:首先,从人生意义和人生目标的高度,审视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的长期价值,尽可能删减不必要的事件;其次,对保留下来的事件,大幅延长原先的估计时间,为未曾预料的事件复杂度和意外事件留出足够的空间;再次,明确工作和时间的界限,尤其不要把工作带入生活,把生活交给享乐主义现在取向;最后,增加主动式的闲暇时间,减少被动式休闲,重新设计自己的业余生活。
立即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