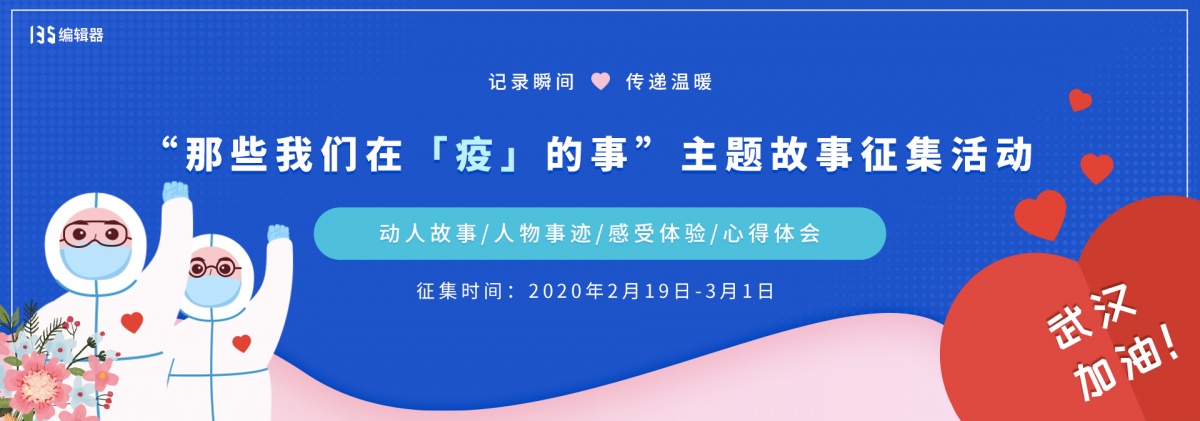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认为这场新型冠状肺炎有其特别性,这也是一直没有写关于这次新冠肺炎相关文章的原因。请注意,我只是在说这场疫情的普通与平凡,并没有说它不严重,我当然承认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当然看到了无数鲜活的生命在这场事故中遭受的令人悲痛的罹难,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次疫情与以往任何人类历史中的灾难并无不同,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过无数次,以战争、瘟疫、洪水、地震、思想运动等不同的名字出现,而且在未来依然还会继续发生。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认为这场新型冠状肺炎有其特别性,这也是一直没有写关于这次新冠肺炎相关文章的原因。请注意,我只是在说这场疫情的普通与平凡,并没有说它不严重,我当然承认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当然看到了无数鲜活的生命在这场事故中遭受的令人悲痛的罹难,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次疫情与以往任何人类历史中的灾难并无不同,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过无数次,以战争、瘟疫、洪水、地震、思想运动等不同的名字出现,而且在未来依然还会继续发生。
没错,依然以不同的名字,同样的形式继续发生,而人们的反应和看法也依然会一如既往。

如果一定要说这次灾难与以往的差异性,我想唯有一点,那就是这场灾难发生在如今这个时代,发生在一个网络信息化极度成熟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这次疫情情况的同时,也可以聆听到任何一个角落对此发出的声音。当我们同时听到这千千万万个不同声音时、当所有人以一个观察者+参与者的身份存在时,其吊诡性就出现了。
那些温驯的面容变得狰狞,那些冷静的心绪变得狂热,那些平凡的事物变得崇高,那些理智的双眸变得盲目,那些常识的认知变得颠覆,那些亲密的关系变得遥远,那些熟悉的规则变得陌生。
在这一时刻,这个世界看似面目全非,其实却是本相毕露,那些恐惧、贪婪、自私、狭隘、无知、空洞都一览无余地暴露在白日之下。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里阐述的一些论点是“反社会”的,某些人看完一定会勃然大怒,但其实这些看法并不是什么新鲜开拓性的论点,甚至可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我并不想对此作出过多的解释和辩护,因为阐述这些基本性的“常识”对于很多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说已经是浪费时间,而对于那些混沌无知的人而言,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接受,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力与思辨力,永远停留在原始思维。
人们总觉得读史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但如果历史读的够多的话,就会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因为几千年来进化的是科技却不是人性,人性内核一旦在遭受到外界冲击后,自然就会剥离被文明粉饰的外壳,展现出最原始、最真实的面目,这也就是历史总是不断轮回的原因。如果你去详细了解过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灾难,无论是十字军东征、中世纪黑死病、西班牙流感、切尔诺贝利事件、埃博拉病毒、神户地震,你都会发现这次新冠肺炎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前人所经历过的,哪怕是在一些虚构的作品中,你也可以窥见这类事件的始终。

在这次疫情中,有两部电影被反复提及,一个是韩国导演金成洙的《流感》,一个是美国导演斯蒂文索德伯格的《传染病》,两部电影用不同的手法为观众呈现出了一场疫情中社会、国家、个人的真实反应,舍弃某些经过加工的戏剧冲突,你完全可以将这两部电影当做一个纪录片去观看,这次疫情如今还没有结束,但电影已经结束,我甚至恶作剧地猜想会不会有某些“先知”会以电影情节去预测事件的发展。
《流感》是标准的商业娱乐片,以灾难片+惊悚片的题材为我们呈现出一场流感在韩国引发的动荡。为了符合灾难片的叙事节奏,流感在其中被设置为极高传染率与高速爆发性,感染的人往往很快就不治身亡,韩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些紧急甚至极端的措施进行应对。剥离其中某些剧情需要的娱乐因素,你会发现很多疑惑都可以在电影中得到印证。

在疫情最初,很多人批评武汉政府对于疫情的披露不及时,而后武汉市长周先旺先生在一次采访中回应:对于疫情的通报要符合《传染病防治法》,作为政府必须得到授权后,依法披露,引起民众对这一说法的巨大质疑。在《流感》中,你可以看到韩国总理对于这一事件的态度,在议员提出要将事件对外公布时,韩国总理如此回应:“人类在危机面前是无法冷静的,如果宣布了,人们就闹翻天了,反而比病毒更加可怕。”
没错,比起流感也许民众的恐慌会给这个社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所以我觉得在大家质疑武汉市张周先生对事件披露是否及时时,更应该思考的是周先生对疫情披露的时间点没有使其造成更大的伤害(这种伤害包括病毒的传播和恐慌会引起的动荡)?
当然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因为我们没办法去证实另一种可能性,可是往往思考的方式与宽度比答案更有价值。

对于传染病的控制手段,自古以来最有效的就是三种方法: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武汉封城,无疑采取的是控制传染源的手段,可是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对于武汉市未被感染的人群来说,是不是存在巨大的危险性?如果隔离措施不当,会不会在武汉市内交叉感染造成更多的病患?(这也是日本撤侨官员因为隔离不当导致一人染病而自杀的原因。)
那么进而又引出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果承认封城会对一定健康的武汉市民造成危险,那么此举是否有悖伦理?武汉市民是否存在被迫地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我们由此可以想到那个著名的道德困境——电车难题:在失控的火车轨道上,你是救一个人还是救五个人?人命可否以数量去衡量?
在《流感》这部电影中,ZF 官员将病毒高发地盆塘区进行封锁隔离,设置治疗检查大本营。但单方面推行的隔离措施引起医生和民众异议,医生反对此举认为如果将感染者和可能感染者放在一起的话,感染速度会急剧上升,感染率百分之五十的病毒会造成20万盆塘市民丧生,韩国总理对此回答:“如果不采取此举,则会造成韩国人民(5100万)的百分之五十丧生。”

韩国总理选择牺牲一部分盆塘市民来守护整个大韩民国,韩国总统得知此举时反问道:“难道盆塘市民就不是大韩民国的国民么?”
正如前文所言,这是自古以来的道德困境,注定不会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答案,前一段时间引起媒体激烈讨论的《奇葩说》议题:“在一场大火中,是救一幅名画还是救一只猫?”正是对于电车难题的改编延伸,李诞在节目中持反方观点,他认为应该救猫,在其辩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这些为了一些宏伟的事业、远大的目标而牺牲别人的人,频频地让我们这个世界陷入大火。”
李诞的说法也许在这一事件中并不适用,甚至很多人都会认为对于封城这一行为完全没有探讨的必要,所谓的探讨在严峻的形式面前只是书生式的迂腐和优柔寡断。但持如此说法的人,那只是因为你不是“城中人”,你只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我想说的是,对于这类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但对于这类问题的探讨,却正是人文主义建立的基石,而只有人文主义的建立,“人”才为人。
与《流感》偏重商业娱乐片不同,《传染病》则更为严谨、客观,片方请来了哥伦比亚大学感染和免疫中心的教授作为电影的医学顾问,学术般地为观众科普了病毒传播过程、基本传染指数等一系列科学问题。擅长群像式拍摄手法的导演斯蒂文索德伯格,在这部电影中更是为我们呈现出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职业的人物在面对疫情的真实反应,其中有冷酷的政客、前线不幸染病的医生、投机的商人、无人问津的患者...... 千姿百态的众生相跃然纸上。

其中有两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一是劳伦斯费仕伯恩饰演的疾控中心负责人奇弗医师,得知病毒的高危性后,在公布疫情前夕将消息透露给自己的女朋友让其尽快逃离芝加哥,而因此遭受到“利用职权为身边人谋利”等一系列指控。
这使我想到了李WL医生事件,2019年12月31日李WL在意识到新冠肺炎的严重性时,在武汉大学临床04级班级群里发布消息说:“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冠状病毒”,提醒同为临床医生的同学“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三天后,他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而被辖区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训诫。2020年2月7日,医生李WL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

至此,全网一片哗然,指责武汉市相关部门未对其言论有所重视导致了“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牺牲及疫情的大面积扩散,那张训诫书也将相关部门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李文亮医生由当时的“造谣者”变为了可敬的英雄。
但是,在我们缅怀李医生的同时,却有几个问题该思考:李文亮医生到底是不是造谣者?相关部门的训诫是否合理?李文亮医生到底是不是英雄?
如今看来,李医生当然不是造谣者,他以一个专业医师的身份第一时间对外发出了警告。但是试想,如果在另一个时空、在一个病毒存在并在起初就得到有效控制的时空,李文亮医生对民众而言还是不是造谣者?

而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相关部门公布的通告如下:“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公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观察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举行处置惩罚。”
从通告上看,如果是在当时疫情未被权威部门证实的情况下看,李医生被有关部门训诫确实合法,这也是避免社会秩序造成影响所采取的必要举措。正如前文所言,在某种情况下,哪怕信息属实,但民众恐慌所造成的危害也许会比病毒更为严重。可是相关部门的做法虽然合法,但是否合理?对于一个专业医师于班级群聊天所发出的内容,其举措是否过于敏感、武断?
而且从通告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文亮医生是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前文有所提及李医生发出警告的群是武汉大学临床04级的班级群,也就是说是他的私人同学群。这也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在私人群对亲朋好友发出警告的李医生到底算不算英雄?
那么进而又将引出一系列的问题:英雄的定义该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英雄?今世还值得英雄出现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传染病》这部电影中另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则是关于发国难财的事件,裘德洛饰演的独立记者,与药商勾结后在其博客上大肆宣扬存在病毒特效药——连翘(一种中草药制品),导致市面上的连翘被抢购一空,甚至在某些药房引发暴行。这部神预言的电影很难不使得我们想到前一段时间的双黄连事件,而更巧的是双黄连口服液的成分中恰好正有连翘。
1月31日晚,人民日报于微博发表“31日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引发全国对双黄连口服液的抢购,甚至双黄莲蓉月饼也被抢购一空。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与民众的愚昧。
很难想象这么荒诞的事件竟然源于最权威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如果官媒传递的信息都无法做到真实准确,那么民众又该靠什么获取信息、信任又该如何依靠?而且在这样一个话语权被掌控的机体下,如果官媒的公信力丧失,则会导致民众对一系列媒体、学术机构等都丧失信任。
以此观之,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下新闻自由与新闻道德?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民众真的如此愚昧么?
是的。
在古斯塔夫勒庞贝的《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出,群体的形成意味着个性的消失,展现出一致性的低智商、情绪化、盲目性,所有人都屈从于一个群体性的目标和价值观,哪怕这个目标再为荒谬。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官媒报道后,所有人都在议论双黄连口服液,暗示性在此产生、群体就此形成,原本作为个人的独立意志和理性也随之丧失,所有人都在以双黄连口服液为最终目标,无意识的人格在此时起到指导性的作用,进而表现出一致性的狂热、愚昧、冲动等特征,闹剧就随之发生了。

《传染病》中出现了在药房对连翘的打砸抢的行为,幸而在双黄连抢购的事件中此类行为并没有发生,但不要以此错误的认为本国国民具有更高的文明性,在我看来只是侥幸,还记得钓鱼岛事件中街头对日系车、日料店的打砸抢么?
在另一部与疫情相关的巨著《鼠疫》中,加繆对人性的愚昧有过另一番表述:“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我们在这次疫情中听过、见过太多愚昧,双黄连事件只是沧海一粟。
传闻说,这次疫情是武汉实验室小三上位故意泄露,于是人们开始谩骂权贵;
传闻说,抽烟和烟花爆竹能防止肺炎,于是人们拼命吸烟;
传闻说,病毒缘起是武汉人民吃蝙蝠,于是人们开始攻击武汉人民该遭天谴;
传闻说,动物可以携带病毒,于是相关社区、组织便开始捕杀猫狗......

人们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了空前的无知和狂热,在其中最令我愤慨竟然是捐款问题,本是善意的捐款在此时却沦为了做人的“义务”和道德的“检视”,捐款的人高尚,不捐款的人卑劣;捐多的人高风亮节,捐少的人厚颜无耻;捐的倾家荡产的人流芳百世,捐的留有余地的遗臭万年。
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探讨捐款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理解另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税收”。税收是指国家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强制、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规范形式。 它是公共财政的主要来源,其职能主要用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国家公务员工资发放、道路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医疗卫生防疫、文化教育、救灾赈济、环境保护等领域。

看到这里我想已经不必再过多解释,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作为一个依法纳税的公民,已经履行了对国家的义务、已经做出了对救灾的贡献,完全没有必要再进行捐款。那么捐款是否还有意义?当然有,但它只应该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善意的表达,对,只是如此,完全不该掺杂其他任何附加价值,这也就是佛家讲究的财布施。
而且我们必须明白,主动表达善意和被呼吁表达善意甚至被要求表达善意是完全两个性质。可如今我们看到的现状却面目全非:某些组织厚颜无耻地募捐、相关企业部门对职工的强捐、民众对公众人物的逼捐等等,捐款已经沦为某些人别有用心的工具。
而且对于捐款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是,助人为乐和助纣为虐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从某种角度上看,给灾区捐款和给路边乞丐施舍钱财是一个性质,在《暗访十年》这本书中,作者针对乞丐问题写道:“任何一个乞丐,没有加入丐帮组织,是完全不可能在城市乞讨的,给乞丐钱,只会纵容这种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思想。那些一直怀有“爱心”,给乞丐钱的“善良”之人,因为你们,城市里的乞丐越来越多,而遭受采生折割的儿童,也不断出现。助纣为虐,与谋财害命何异。 ”(请注意,这里谈的问题是针对钱款,而并非物资。)
对于《暗访十年》作者提出的观点,我们见仁见智。

最后,我想再聊聊这次疫情中的歧视问题与个体的关系。
新型冠状病毒于2月11日被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正式命名为“SARS -CoV-2(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而在此之前,在国际上仅称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或中国冠状病毒、武汉冠状病毒。这也曾引起了民众的热烈抗议,指责其叫法存在歧视性。
在我们看到华人脆弱的玻璃心时,也该思考一下个体定义与歧视的关系。
我们在纠结他国对新冠病毒的叫法时,顿时化身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可是却忘了我们前不久还在疫情爆发时,对封城前夕出逃的武汉人一片诅咒谩骂;运往重庆防控中心的口罩,被大理在中途截获强行征用;某小区担心病毒传入,禁止医护人员下班回家......
可能在所有人都人人自危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什么才是世间最准确的存在单位。

在种族中,白种人歧视有色人种;在国家中,欧美地区歧视亚非地区;在财富中,有钱人歧视穷人;在中国内,北上广的人歧视“乡下人”、南方人歧视北方人、汉族歧视少数民族、村东头歧视村西头、小儿子歧视大女儿....... 我们从人种、洲际、国家、地域、职业、财富、民族、宗族一路走到最后,发现“种族歧视”以各种变相的方式无所不在。
在己身利益遭受触犯时,我们总是很容易遗忘不久前我们还坚信拥护的一些事物与概念。如此看来,世间或许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体”,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有“我”与“他”之别。
那么,作为人的个体才是世间最准确、最真实的存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所谓的“集体”、“共同体”、“党派”、“公司”、“学校”、“民族”、“国家”,实际上都只存在于想象当中,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对于这一概念进行解释:“
第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分散的、相互没有个人联系的,但他们能够通过各种媒介“想象”出一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第二,这个共同体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它一定是有边界的,因为在它之外存在着其他类似的共同体,由这个边界就产生出“主权”的概念;
第三,这个“主权”的概念是至高无上的,它并非只是狭义的领土主权,而是这个广义的共同体作为集体本身就有一种基于想象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第四,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想象中内部“平等的社群。”

有些晦涩?好,我们再来看看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提出的对想象共同体的判断方法:
“怎么知道某个实体是否真实?只要问问自己它是否会感觉痛苦。放火烧了宙斯的神庙宙斯不会感觉痛苦;欧元贬值,欧元不会感觉痛苦;国家在战争中遭到击败,国家也不会真正感觉到痛苦。然而,如果士兵在战争中受伤,他确实会感觉痛苦;饥饿的农民没有食物可吃,会感觉痛苦。这些实体,则属于真实。”
是的,很多你一直秉持、坚信的概念和事物,或许一点意义也没有。
如果看懂了这个概念,则相应的会引发出很多问题:
民族主义有没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个人出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而“生为某人”,就一定要终身背负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吗?
它应该规范、要求其成员无条件的服从并在某些境地作出牺牲吗?
在虚构想象中高谈更为扯淡的荣耀、崇高、光辉、伟大、神圣..... 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挺虚无,挺有意思。

聊到这里也差不多了,这篇文章陆陆续续写了很久,但到最后依然并不完善,因为想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很多东西又没办法详尽、准确地表达出来(原谅我笔法的拙劣),其实我知道写这样一篇文章除了再次梳理一下自己的想法,一点意义也没有,作为七千字的长文,相信是没有几个人有耐心一直看到最后的,但没有关系,因缘际会,随遇而安。
曾经和一个传说中很牛逼的茶者聊天,我问了她很多关于普洱茶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过于刁钻,类似于“矛和盾”的问题,但并非存心刁难,确实是我心中的真实疑惑。她当时神色有些不悦,有些问题未予回答,最后以一个长辈教训晚辈的姿态对我说,我的知识体系太混乱了,应该看一点大部头的书籍,应该建立“Basic Knowledge”——基础知识框架(是的,当时她说的就是英文)。
其后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Basic Knowledge”?前不久一个朋友给了我答案,这也是我这篇文章通篇都在阐述的一个概念——开放性。
没错,开放性——对一件陌生事物或概念的接受度、思辨力、宽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