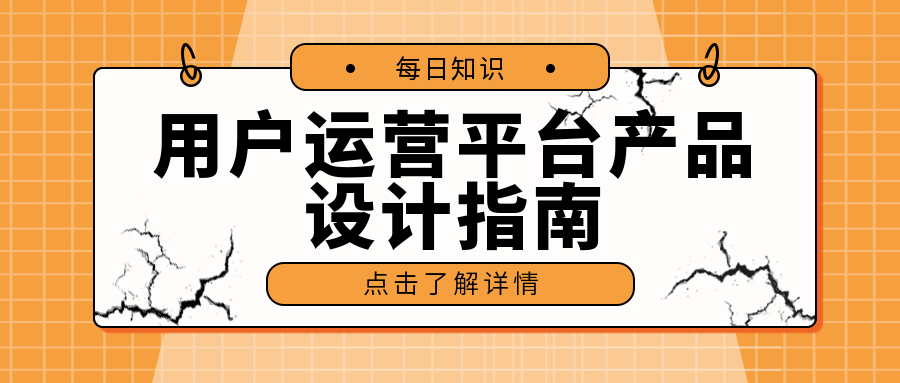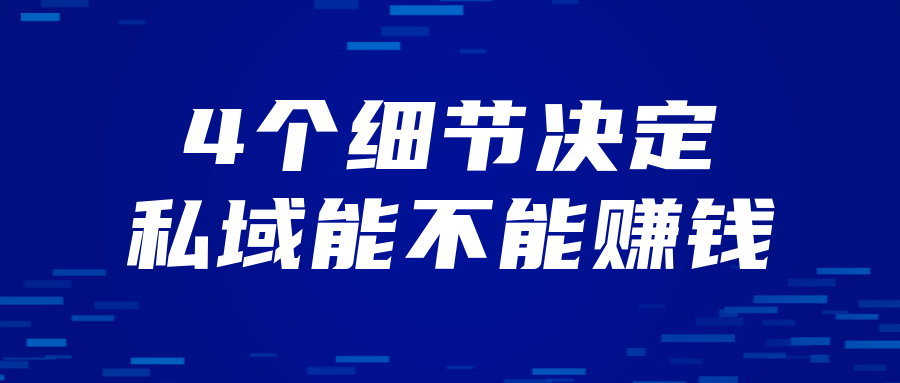不得不承认,时间管理上的低能是我们的硬伤
“中国人的‘时间商’有限。我们直面时间时展现出的态度,暴露了这个社会隐藏至深的沉疴和隐患。”
只要有机会坐火车,李子勋都会格外留意邻座“车友”的一举一动。通过过去几年的乘车经历,他发现,能在火车上“聊大天儿”的人越来越少了。
“看书的、沏茶的、泡面的、听音乐的,当然最多的还是低头玩手机的。”李子勋说,过去还能和邻座、邻铺的人搭两句嘴,开个玩笑,冷不丁还真能遇上几个交心朋友,但如今的车厢里,却满是“时间满档”的匆匆过客。
“把自己搞成忙人样儿,不就是现在所有人的状态吗?”他有时候会这样反问自己,不过更多时候却是向社会发问:
抓紧时间是好事,但刻意排满日程真的就是现代生活哲学?
安排时间是好事,但是瞎忙真的就意味着在享受生活?
反对浪费时间是好事,但过于精算那些需要节省下来的闲散时光,真的是活得精致、过得洒脱、出落得成功的一种佐证?
最后他想通了。
“中国人的‘时间商’有限。我们直面时间时展现出的态度,暴露了这个社会隐藏至深的沉疴和隐患。”
对时间的低能管理,是中国人的一大硬伤
曾经有心理问题患者找到李子勋:“李老师,我常年出差在外,过年回家女儿都不认得我了,这可怎么办?”
这个被李子勋日后反复讲述的亲子问题案例,最终以“李老师”对求助者的批评和建议结束。“你既然把99%的时间花在工作上,那你也就没有准备选择做好父亲这个角色。在工作上你可以是工作狂,是成功者,但在生活中你不可能承担起一个正常父亲所应承担的责任。”
罗振宇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在李子勋看来,“罗胖”关于“做时间的朋友”的观点固然精彩,但他更愿意细化我们每天与之打交道的这个“朋友”的具体身份和细节特征。
“有时做心理分析我会遇到这样的求助对象,她说自己为了儿子的教育费尽了心思和时间:‘每天我都和儿子待在一起啊,但我俩间的关系却感觉越来越远。’我就问她:‘除去叫起床和喊吃饭,你和儿子有过交流吗?会不时和他谈话吗?’”
对方摇头,这让李子勋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虽然有时我们愿意和时间做朋友,但凡事并不是只花费时间就能做好的。
“你每天和儿子待在一起,你每天伏案温习功课,你每天回家照看老人,但你对时间这个朋友的诚意真的足吗?够吗?你的有效时间哪儿去了?”
“中国人肯定愿意和时间做朋友,但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向‘有效时间’这个朋友开诚布公?”李子勋说,“你可能天天都陪着孩子,但那仅限于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沟通和交流,真正能够抵达和触动孩子内心的话,你没时间说,也没那个意识去讲。所以你对有效时间的利用率是零,孩子对有效时间的反向利用率也是零,零零相乘,结果能不是零吗?!”
有效时间的低利用率不仅存在于代际沟通方面。
伴随着中国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李子勋注意到,每年春节返乡时,不少群体对有效时间有着轻视和漠然。“春节返乡回家,无数人美其名曰陪老人,但人在那里,心却飞了。
飞到哪里去了?
飞到红包里去了,飞到‘摇一摇’里去了,飞到有Wi-Fi、有网络的虚拟世界去了,这是在都市务工的白领对有效时间的低利用率;在外赚钱不易,打工者每年回村里一次,探父母、看孩子,这是在外务工后返乡回村的打工者对有效时间的低利用率。”
对有效时间的轻视,引发过诸多社会问题:
无法分配时间探望双亲,让“常回家看看”作为规章条文被写进法律;无法分配时间关注彼此内心,让“无解代沟”的亲子教育问题、“同床异梦”的夫妻关系问题层出不穷;无法分配时间照顾父母/孩子,让农村“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愈演愈烈。
“对有效时间的低能管理,是当代中国人的一大硬伤。”李子勋说。
你对待时间的方式和方向,决定了你个人发展和前进的空间。
今年1月,江苏大学电气学院研究生史国平在参加完师生聚餐后倒在宿舍,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据了解,此次聚会的五桌师生共喝掉18瓶酒,导师在席间对研究生们进行了多次劝酒。
本该徜徉在学术海洋里做学问的年轻生命,却在一次“泛社会式”的“学术应酬”过程中意外中止,这引发不少网友的追问:学生不把时间花在学术讨论上,却花在“加学分、蹭期刊和抱导师大腿”的交际上,这合理吗?
李子勋对此有话要说。
他认为东西方在对待学习、休闲和人际交往的态度上完全不同:在西方学生的观念里,学习摆在首要位置,其次才是爱好或者人际交往;中国学生则不同,他们面对的情况更棘手、更复杂。
李子勋以中国学生在升学过程中遭遇的时间困境为例,系统阐释了中国学生在时间分配方面的无能、无助和无奈。
“总体来说,中国学生的时间是由老师、家长来规范和分配的。在18岁前,我们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备战高考,这事儿压倒一切;18岁后,我们的学生才意识到解放天性的重要性,因为在大学没人管你了,所以才开始本该在幼龄时就做的种种尝试。”
而这仅仅是“学生”这一群体在遭遇时间分配时的中国式困境。
他认为:
中国人花太多时间在移动互联网的阅读上,这对深度获取有效信息没太多帮助;
中国人爱拐弯抹角说话,这对彼此合作的开展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没太多好处;
中国人处心积虑地以疏通关系、拓展人脉为借口,取代本该深耕主业、精细钻研的工作态度,这对个人职业生涯的前途没太多促进作用。
“最后你会发现,你对待时间的方式和方向,决定了你个人发展和前进的空间。”李子勋说。
中国人始终强调精英文化,却直接拒绝了缓慢、多元的生活方式。
发现中国现阶段各群体在时间分配方面的问题后,李子勋试图深度剖析这些问题的成因。
在国外,见面打招呼是常态,开会畅所欲言是常态,对生活中细致入微小情调的追寻也是常态,李子勋认为这是有效分配时间的一种方式。
“和陌生人问好让你的一天从微笑开始,开会快言快语让工作效率提高,追求生活情趣是在直接提高生活质量。”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停不下”“急匆匆”和“等不得”,则让看似合理分配的时间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新周刊》曾在2010年以“急之国”为题,对“中国人为什么失去了慢的能力”进行过追问。李子勋认为如今的中国社会非但没有解决“慢不下来”的问题,反而在快速向前奔跑的路上愈行愈远。
“国人对时间效率过分看重的心态,从改革开放起就开始出现。”李子勋说。
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像放闸,闸门打开了,人心思变,大家都往前冲,时间被货币化,时间就是金钱,运用时间的效率和生命同等重要。
这当然迅速解决了当时国内积贫积弱的经济状态,但当我们把时间和精力过多投入经济发展时,文化道德层面却被抛在了身后。
“能量向来守恒。所以中国经济上去了,但始终无法腾出过多时间和空间深耕文化和道德领域。现在国人可能也想停下来喘口气,但发现已经停不下来了。
我们的GDP排世界前列,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发展甚至不如新加坡。”李子勋说,“国进民退的一大特点在于,国家经济繁荣昌盛,民众的精神生活却原地踏步甚至退步,这也就是欧美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比不过中国的一大原因。
人家买东西讲的是情趣,是和家人一块儿逛商场的乐趣,而不是像国人一样扫码付款的快节奏生活方式。”
李子勋认为中国社会向来强调竞争,表面上是对时间的争取和最大限度的利用,实际上是对内容多元、悠闲自得的慢节奏生活的否定。
“成功学扼杀了多元化发展,效率论抬高了时间的货币属性。所以我们始终强调精英文化,却直接拒绝了缓慢、多元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时间商”要向德国人看齐
“中国的文化是感性文化,西方人遵循的则是理性文化。中国人用时辰计时,两小时为一个时辰,这其实是非常模糊的概念。西方人对时间的感知是非常强的。”
李子勋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模糊的时间观,让中国人的“时间商”显得比较有限。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西方人对时间观念的恪守和执着。
李子勋记得有一次前往德国开会时,中方人员与德方人员搞联谊晚会。一到十点半,德国人便纷纷退场回房休息。“西方人很少熬夜,他们对身体是非常重视的,虽然不会像钟表那么准,但至少不会晚睡。”而留下嬉闹的全是中国人。
“我认为中国人的‘时间商’是有限的,该休息的时候不去休息,该紧张的时候偏不紧张;需要提高效率快速表达一个意思时,中国人非要拐弯抹角挤出来;需要花时间深耕主业时,中国人非要琢磨那些细枝末节,”李子勋说,“中国人的‘时间商’真的要向德国人看齐。”
立即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