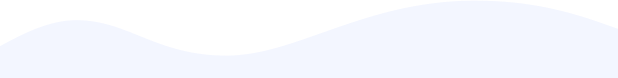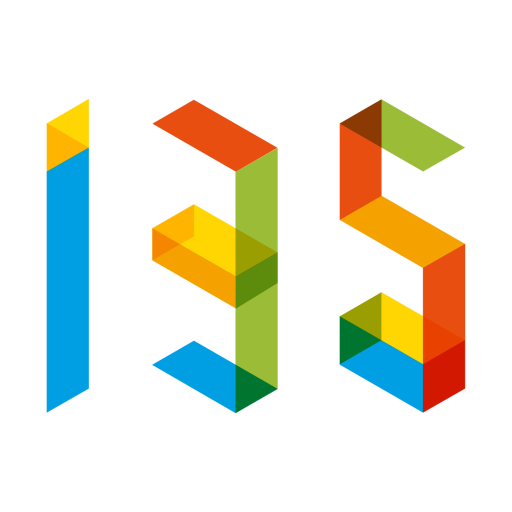温暖冬日回忆散文诗歌文艺蓝色模板




记忆中的童年,似乎都凝结在那些与母亲相守的有限的时光里。比如母亲最喜欢坐在桌边纳她的鞋底儿,每到那时她总会安排我在旁边写字。其实我也不知道看什么书写什么字,就听了她的话坐在那里装出一幅乖乖学习的样子,思绪却信马由缰。耳朵里听着她手中钢针穿透厚厚鞋底儿、绳子被拽的“滋滋”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想:大人们为什么管这鞋底儿叫“千层底儿”,哪里有千层,分明就是四层五层嘛,所以说大人们都爱夸大其词。




后来,我大概是变“坏”了。因为要去外乡里上学,就骑一辆自行车每日里来来回回。也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跟谁学会了打响指、吹口哨,一幅鲜衣怒马的样子骑车在马路上飞驰,更甚至也抽过烟、也喝过酒的。这些“不良行为”终究是被母亲发现了,她很及时得狠狠地给了我一顿棍棒式的教育,致使我“改邪归正”。想想那年冬天,厚厚的衣服里带着伤,内心其实蛮感激她的,亏了她的那顿打,不然我不定会发展成什么样的“痞子太妹”呢。




母亲总想再替我做些什么,我就由她量力而行,前提是不能劳累,要保持身心愉悦。她故作潇洒的说,没事儿,现在啥也能做得了。我想,母亲做个简单的十字绣鞋垫儿应该不费力吧。
母亲总想再替我做些什么,我就由她量力而行,前提是不能劳累,要保持身心愉悦。她故作潇洒的说,没事儿,现在啥也能做得了。我想,母亲做个简单的十字绣鞋垫儿应该不费力吧。